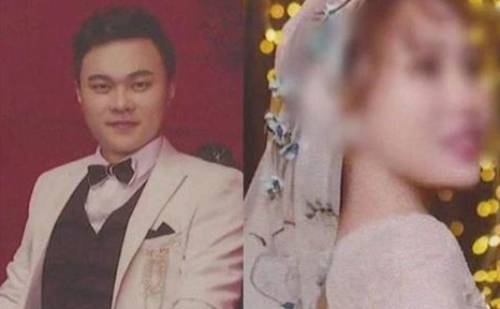学生上学爬悬崖边10米高木梯领导称没钱修路|天梯|上学|扶贫_飞外新闻
红鱼洞组的两部“天梯”只是斜靠在悬崖边,两端并不固定,余启运正在向上爬
回家途中的艰险路段,背上的孩子向前张望
多人险坠崖丧命 异地搬迁方案遭村民反对
探访桑植“天梯”上学路
《法制周报》实习记者 余修宇 文/图
核心提示
湖南省桑植县苦竹坪乡张家湾村是个并不出名的村子,本乡都很少有人知道从山外进入村子的方法。
近日,央视关注该村15岁学生余启运爬“天梯”上学之后,这个普通村落迅速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。
张家湾村坐落在苦竹坪乡东北角的群山之间,地势险要。该乡只有小学,没有中学,村里的小孩上幼儿园也要家人爬过“天梯”或悬崖接送,有的地方甚至要走两三个小时。
余启运和8岁的妹妹余欣欣都在距家30多公里的龙潭坪镇读书,每次回家,妹妹都会嫌路太难走而大哭。所谓的“天梯”,只是一架木梯,两端斜靠在悬崖边,“天梯”后面就是陡峭的深渊。以前,曾有家访的老师从此摔下险些丧命。
张家湾村村主任刘兴阶说:“一下雨孩子们就不能上学,山路太滑,要是连续下雨,孩子们就一个多星期不能上学。”
山外,只有两三米宽的公路旁有许多沿路而砌的坟墓。村民们说这是当地一种习俗,沿路修坟可以旺丁生财。这或是村民祖祖辈辈对通路渴望的一个缩影。
对当地政府而言,为悬崖绝壁之上的90几个村民修公路是“不现实”的。4月15日,县里的技术人员进行了实地勘测,将选择用水泥台阶替换木制“天梯”或者修建简易公路的方案以减轻其危险性。
●这两架“天梯”加起来有10多米高,靠在悬崖峭壁之上,没有任何固定设施,后面则是七八十米的深渊。半年前,余欣欣差点掉下悬崖,所幸母亲眼疾手快将其抓住。
●苦竹坪乡党委书记熊东见给村民算了一笔账:“如果修路,拉通全村7个组至少30公里,保守估计一公里50万元,共1500万元,后期的维护保养资金又将是一道难题,谁来买这个单?”
●张家湾村村主任刘兴阶介绍:“现在的情况是,年轻人希望能搬出去,中年人则不希望搬迁。”
“天梯”已有几百年历史
余启运是张家湾村红鱼洞组人。为照顾兄妹俩上学,母亲吴成香在龙潭坪镇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子。每个月,余启运会回家一两次,通过两部“天梯”只要一两个小时,绕行山路则需要四五个小时。
4月11日,记者和余启运一起回家。他要给朋友带东西,由母亲和妹妹余欣欣坐在记者车上先走一步,他骑摩托车追上我们。虽然爬“天梯”比绕行节省时间,但在放学后赶在天黑前回家仍然来不及,余欣欣每每提到回家便要哭。无奈之下,去年年底,家人给余启运买了一辆摩托车,先骑一段路,可以省点时间。
按照相关规定,15岁的余启运不能骑车上路,但他说:“没事,我已经习惯了。”一次在山下的弯道上,另一辆摩托车和他的车相撞,幸运的是两人均无大碍,但他现在仍心有余悸。
一个多小时后,到达山脚,余启运将摩托车寄存在朋友家。一行人从山脚沿小路向山上走,有些路段只能爬行。半个多小时后,“天梯”才出现在记者眼前。这两架“天梯”加起来有10多米高,靠在悬崖峭壁之上,没有任何固定设施,后面则是七八十米的深渊。半年前,余欣欣差点掉下悬崖,所幸母亲眼疾手快将其抓住。
爬上“天梯”后,还要十几分钟才能走到余启运的家。
余启运的爷爷余大桃告诉记者,这两架“天梯”是他和村里的几个老人制作的。在该村,制作“天梯”的历史已经有几百年,代代相传,三五年更换一次“天梯”。因身体不好,72岁的他和66岁的老伴杨云南均已多年未曾下山。
据了解,张家湾村占苦竹坪乡面积的四分之一,地广人稀,村外仅有一条简易公路通往村子。该村曾被县、乡政府列为“建设扶贫村”,今年又将其列为“高寒山区村”。全村共7个村民小组,组与组之间均有大山相隔,想把全村走遍,得要两天不眠不休。
余大桃说:“张家湾有四险,两处‘天梯’两险路。‘天梯’共48步,红鱼洞组36步,张家湾组12步。”这句话在村里广为人知。与之对应的四险为红鱼洞组两部“天梯”共36个木阶;张家湾组一部“天梯”12个木阶;窝塘组一条险路高十几米;水竹园组一条险路80度斜坡,身后是300多米的悬崖,曾有一家访老师在此摔落,幸好有绳子绑住,同行人把他拉了上来。
张家湾村共有在校学生60人,孩子们上学的情况分为两种:一种是寄宿上学,家人在学校附近租房居住;另一种是接送上学,每天早晚由父母或家人爬山接送孩子。张家湾村寄宿学生有三四十个,需接送上学的学生有9人,另一些随打工父母在外地上学。
余启运和余欣欣都是寄宿上学的学(户籍所在地怎么填写?户籍所在地是指我国居民户口簿登记所在地,一般是指出生时其父母户口登记地方。按照户口登记管理条例,公民填写户籍所在地,应该填写到户籍管理机关所在地,即城市户口的应该填**省**市(县)**区;农村户口的应该填**省**县**乡。一般在填写户籍所在地时,只填写到县就可以了。)生。余启运告诉记者:“村里有些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学生,如果不在同一所学校,只有过年时才会相见。”
谈及山外的生活,余启运说:“我将来一定要走出去,老了再回来。”
靠山吃山 :打粽叶、砍杉木
传说有人在山洞里见到有许多红色的鱼游出来,红鱼洞故此得名。
50年前,红鱼洞组只有刘、王两户人家。后来有人搬迁过来,现共有8户村民,除去外出打工的人,常住18人。余启运的父亲余佑全小时候搬来,在这里建起了一栋木屋。
山上有大片的野生粽叶,每年六七月份到次年3月,都是粽叶采摘的旺季。这个时候,余佑全常在凌晨4时左右就起床打粽叶,每天采摘70多市斤的湿粽叶,用火烤干后运出去卖,能卖一两百元。
因为山里不通路,余佑全只好把粽叶攒到一定数量后,用扁担运到山下的人家寄存,达到一定数量后再找车运走。
砍伐杉木也是余家的主要经济来源。砍下的杉木要将其剥皮洗净,待雨季来临之时,将杉木拉进水中,使其顺流而下,运到山脚。20根杉木一组,一般能卖四五百元。记者提出要看看他砍伐杉木的地方,“那地方太远了,得绕到山的另一面,要走几个小时。”
虽然土地不多,但人口稀少,余佑全家分得了两亩田。余家牛棚旁养着一个蜂窝,蜂蜜留够自用的都拿出去卖。余佑全说:“山里的东西很多,我们靠山吃山。”他偶尔会背着竹篓在山里采药,运气好能遇见五步蛇,一条大一点的五步蛇能卖到两三千元。
没有自来水,余佑全将拇指粗的水管插进山上泉水的石缝内引水入户。
几年前,村里人还出资购买变压器,请电工牵电上山。余佑全家的家具和家用电器并不多,沙发、电视及音响,都是他从山下一次次扛进来的。
因常年负重,余佑全的肩膀长满了厚厚的老茧。
异地搬迁提案陷僵局
“现在的问题,说到底还是路的问题。”4月11日晚,苦竹坪乡党委书记熊东见带领一队乡干部上山,到余佑全家和村民们商量解决方案:“但为红鱼洞的18人修一条路是不现实的。”张家湾村全村没有一条公路进村,熊东见说,如果修路,全村都要修,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。
他给村民算了一笔账:“如果修路,拉通全村7个组至少30公里,保守估计一公里50万元,共1500万元,后期的维护保养资金又将是一道难题,谁来买这个单?国家并没有把村道的后期维护资金列在相关计划之内。”
另外,即便投入使用后,红鱼洞、白塘坪、风相凼、水竹园四个组加在一起只有90几个人,只有四五百亩的水田和旱地,后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不大。据统计,张家湾村共398人,除去外出打工者,常住人员只有186人。
“如果要修路,30多公里的路要放炸药开路,碎石等会对生态造成破坏。”熊东见说,“我们算了环境账、经济账,都不划算。”
熊东见提出一个想法,想从红鱼洞组开隧道引水。2011年,乡里在窝塘组曾打算搞“苦竹坪引水隧洞工程”,打算挖通两条隧洞,一条取生活用水,另一条取灌溉用水。但因资金问题,只完成了其中一条生活用水隧洞,投资80万元,洞长970米。原打算为窝塘组修建的横跨两山之间的桥也没有建成。熊东见希望可以从红鱼洞组开通一条新隧洞,“这样一方面解决了灌溉用水的问题,另一方面可以解决交通问题,但这是远期方案。”
因此,熊东见又提出了异地搬迁的建议:“我们和县里汇报了,可以异地搬迁,如果搬到苦竹坪乡镇,医疗、卫生、教育相对来说都要好一些。”乡亲们并不买账:“搬下去后我们吃什么?”
按照现有异地搬迁政策,人均补贴5000元,特殊情况从9000元到两万元不等。
以余启运家为例:余家6口人共3万元,政府安排建房土地,但建房资金8万~10万元要自己出。
张家湾村村主任刘兴阶介绍:“现在的情况是,年轻人希望能搬出去,中年人则不希望搬迁。”异地搬迁陷入僵局。
孩子们上学的问题怎样解决?6月的雨季即将来临,涨水之后,水会漫没山下公路,“天梯”和险路也非常湿滑,险情常有发生。
4月12日,桑植县政府发文,针对村民出行难的问题,由县财政局、交通局、发改局、扶贫办各出资5万元,共计20万元资金,由苦竹坪乡党委、政府和张家湾村村支两委组织实施,以最快的速度修好便道以方便村民出行。
“将现在的木制‘天梯’替换掉,这个任务要在6月洪水来临之前完成,除此之外,其他组的险要地方也会有一些变化,但变化不会很大。”熊东见称。
记者手记
修好路,就不用冒着风险回家
实习记者 余修宇
4月11日,张家湾村红鱼洞组颇为热闹。省内七八家媒体记者齐聚于此,比红鱼洞的村民还要多。当晚,乡党委书记熊东见和乡干部到余家找到我们,每个人头上都带着豆大的汗珠,据说他们跑上山只花了15分钟。
夜里,因人多床少,我和余启运挤在一张床上,他对我说:“我将来一定要出去,最多老了再回来。”我当时还不解15岁的孩子为何有如此想法。
4月12日中午,我因之前听闻张家湾村共有4险,红鱼洞组的两部天梯仅为其中一险,便决定要去一探究竟,约了村主任刘兴阶做向导。他告诉我,剩下的三险一个下午走不完,随即他建议:当天下午先绕到山的另一面过隧洞去看窝塘组的险道,第二天再去看另外两处天险。
第二天早上6时30分,我们出发,因搭车不便,乡里特别安排专车送我们至山脚。下车后,有十几个村民在等我们。刘兴阶说,考虑到记者要拍照,他特意跟当天准备背肥料回村的村民约好一起回村。
刘兴阶说,水竹园组只有一条险路。一路上,我问了好几次:“这就是那条险路吗?”回答是:“还没到,险路比这难走多了。”
突然,行进的队伍停下来,扛肥料的村民卸下肥料,背孩子的都把竹筐取下来。刘兴阶告诉我,就要过险道了,负重的村民决定休息一下。“下雨的时候,这里最容易出意外,常有野兽掉下山去,有时村民扛的肥料也会掉下去。曾经有个老奶奶摔了下去,幸好被树木挡住,但摔成了脑震荡。”
我仔细查看了这条险路,近80度的斜坡,只能容下双脚的逼仄山路,身旁蓬松的山草,身下就是陡峭的悬崖。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。
在这里,回家是一件必须要认真对待的事。
这里位于八大公山天平山的南边,与旅游风景区只有一山之隔。一路上,我不只一次被问起能不能修路。我只好说:“乡上说可能会给大家修个便道。”刘兴阶低声告诉我:“大家都希望路能修通,这样孩子们上学方便了,大家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风险回家。”这时,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余启运那么坚定地说一定要走出大山。
- ·学生上学爬悬崖边10米高木梯领导称
上学相关报道
- ·学生上学爬悬崖边10米高木梯领导称
爬相关报道
- ·学生上学爬悬崖边10米高木梯领导称
悬崖相关报道
- ·学生上学爬悬崖边10米高木梯领导称
10米相关报道
- ·学生上学爬悬崖边10米高木梯领导称
高木梯相关报道
- ·学生上学爬悬崖边10米高木梯领导称